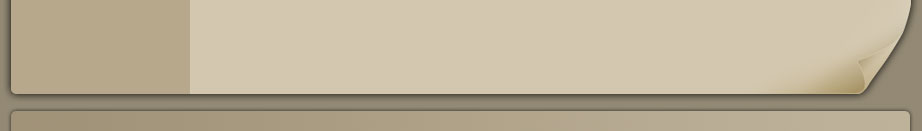在紹興城東箬簣山麓���,有一湖名曰東湖�����。我來(lái)紹興一年有余��,亦曾聽(tīng)說(shuō)過(guò)“天下第一水石盆景”�,卻一直沒(méi)有機(jī)會(huì)得以見(jiàn)之。這次�����,借著校自管會(huì)名人故居走訪的機(jī)會(huì)���,我終于有機(jī)會(huì)來(lái)到了東湖��。這日天氣并非是艷陽(yáng)高照�����,下著雨而游園的積極性不減分毫�����。雖不是杏花微雨�,亦沒(méi)有撐著一把油紙傘��,東湖的詩(shī)意卻在這忽下忽停的雨中更添了幾分���。
蒙蒙的細(xì)雨氤氳著�����,還未走進(jìn)便在蒙蒙朧朧中望見(jiàn)了景區(qū)外一塊巨石上刻著“東湖”這兩個(gè)大字����,一下子就使人想要迫切地走進(jìn)參觀。我們沒(méi)有導(dǎo)游或是宣講員��,在景區(qū)內(nèi)走走停停����,四處游逛,倒顯得更為自由與愜意���。
在東湖����,我最感興趣的是青石板鋪成的道道小路以及那一座座橫跨兩岸的各式古橋����。走在小道上�����,兩旁或山或水或樹(shù)����, 青石板路不似鋼筋水泥筑成的馬路那般冰冷而浮躁��,它帶著江南水鄉(xiāng)特有的美����,每一塊石板����,都似一個(gè)悠長(zhǎng)悠長(zhǎng)的故事,帶著歲月匆匆�����,見(jiàn)證了歷史流淌���,踏步其上���,便能讓人沉醉。我想����,青石板大概也是有生命的吧,他靜默著����,在風(fēng)吹日曬中訴說(shuō)著古老的情緒�����,只待那一個(gè)個(gè)能懂的人走近他����。
而一座座古橋呢�����,帶著悠悠古韻�����,與那淙淙流水一同��,如畫(huà)般的美好����。細(xì)細(xì)菲菲的煙雨籠罩著����,使得多少騷客文人駐足觀賞�����,爭(zhēng)相吟詠著詩(shī)文來(lái)贊美�?沒(méi)有分外磅礴的氣勢(shì)��,它更多的是如一首綿綿的長(zhǎng)詩(shī)�,守著橋下之水長(zhǎng)流。你來(lái)或不來(lái)���,欣賞或是厭惡�,這一座座的石橋���,都仍舊立在那里���,不喜不悲,它在歲月中沉淀著�,篩去了浮躁,變得古樸蒼老����,任青苔在不知不覺(jué)中悄悄爬滿了橋。小橋流水,它的美���,在于詩(shī)畫(huà)般絕美的意境���。
而園內(nèi)的亭臺(tái),亦是別具一格�����。聽(tīng)湫亭��、飲淥亭����、香積亭、寒碧亭�,巧妙地對(duì)應(yīng)著春夏秋冬四季。游園恰逢秋季��,是桂花時(shí)節(jié)�����,雖已被風(fēng)雨吹落了滿地���,卻依舊能聞得桂花清香�。香積亭�,顧名思義,就是香氣積累的亭子�����,花易落而香卻不亦散��。桂花雨落���,鋪了一地����,讓我想起了自己曾經(jīng)寫(xiě)過(guò)的一句詩(shī):“桂樹(shù)殘枝雨滌香�����?���!倍螆@時(shí)亦見(jiàn)有兩個(gè)老太太分坐在一株桂樹(shù)之下的一級(jí)石階的兩旁,更加讓人覺(jué)得寧?kù)o祥和����。
東湖除卻景美�����,更重要的是它帶著一種歷史滄桑感�����。相傳東湖所在地原為一座青石山�����,秦始皇東巡時(shí)曾經(jīng)過(guò)此處��,漢代以后曾在這兒采取石料��,它在隨著歷史的推移而變化著����,直至清末時(shí)期����,陶浚宣將其修飾,自然的鬼斧神工加之巧奪天工的人工裝扮���,才有了后來(lái)的東湖��。
在東湖景區(qū)里��,還有一處為紀(jì)念陶成章烈士而建的“陶社”�����。雖曾在抗戰(zhàn)時(shí)期毀于戰(zhàn)火�,它得以重建����,主要用于陳列陶先生的事跡。陶社正中懸掛著孫中山題的“氣壯山河”匾�����,兩側(cè)楹聯(lián):“半生奔走�����,有志竟成��,開(kāi)中華民主邦基�,君子六千齊下拜��;萬(wàn)古馨香�,于今為烈��,是吾越英雄人物�,湖山八百盡增光?!边@是對(duì)陶成章短暫而光輝的一生的贊美,而陶社承載的����,是烈士不朽的愛(ài)國(guó)情。
游賞東湖����、參觀陶社,我們所領(lǐng)會(huì)到的�����,有江南水鄉(xiāng)之美�,亦有名人烈士的精神。陶社愛(ài)國(guó)主義教育基地�����,讓我們?cè)俅渭?xì)品了這一段歷史,再一次為烈士扼腕嘆息����。
而這次游園亦有一些遺憾,比如未能乘坐烏篷船泛舟湖上��,未能進(jìn)入各個(gè)洞中觀賞�,亦因雨天路滑而未能拾級(jí)登山。
該文為文理學(xué)院書(shū)院委員會(huì)游東湖而作
作者 王葉